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第51章 白塔(第1页)
汉州市郊和入城高速交界的地方,有一片被开发区环绕的小镇,路牌上依稀能辨认出“白塔镇”三个字体。
这里只经历过一轮联合集中搜救,救援队甚至还没完全清理彻底这片区域,就被紧急抽调回了市区。而白塔镇从那以后也再没有发出过幸存者求救的信号,哪怕是直升机几次从上方盘旋飞过,也未搜索到一个活人的影子。
白塔镇被一道几米高的铁护栏和市区隔离了起来,显而易见,它的名字由来于这里矗立的一座白塔建筑。
这座塔号称是整座镇子里最高的建筑物,挨着半截废弃铁路。最初是政绩催生的产物,十几年前当地旅游业发达的时候没少赚旅游客的钱。居民嘴里把它吹上天,心里把它当摇钱树。
后来换了领导班子,有人提议把这里拆掉,仿建一座黄鹤楼、滕王阁那样的名楼。但在改建方案刚刚通过不久,感染就爆发了,全世界的城市在一夜之间都衰败下去,没人再搭理这里的一座白塔。
丧尸盘踞在这座镇子上,它们因为久未进食活人而变得焦躁和暴怒,四处搜寻着哪怕一丝新鲜血肉的味道。可怖的嚎叫声在烈烈寒风中被吹散,又落到角落隐匿者的耳中,犹如死亡在它军前吹响的号声。
水荔扬站在铁丝网前,伸手按在上面,似乎已经嗅到了溅在铁网上的鲜血混杂着铁锈的味道。
“我们进城的时候没有经过这里,因为这边是市郊最大的一片开发区。附近几乎所有的流动人口白天都聚集在这里工作,所以丧尸的数量非常多。我们制定过几版救援方案,都没有落实。”
水荔扬说着,忽然抓住了铁丝网上的围栏,双腿用力在上面一蹬就把自己翻了上去。他蹲在围栏边缘,笑着朝洛钦伸出手去:“上来吗?”
洛钦没有他那种叫人赞叹的身手,只能憋屈地搬了几块砖头,拽着水荔扬的手爬上去。围栏上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,他颤颤巍巍地扒在上面,向已经跳到另一边的水荔扬求救:“荔枝,你可一定要接住我。”
水荔扬向他张开双臂,像是要奉送一个拥抱:“跳!”
洛钦闭上眼跳了下去,被水荔扬及时捞住,稳稳落在对方怀里。两人脸颊蹭到一起,水荔扬双手紧紧抱着他后背,十指熨烫的感觉无比清晰。
洛钦脸上烧得慌,急急忙忙跳到地上,故作轻松地整理了一下衣服。
两人翻过围栏的地方还算是隐蔽,刚好被那座白塔和它周围的杂物挡住,所以不会被那群游荡者注意到。但洛钦根本无法想象比这更疯狂的事情——他和水荔扬翻过了安全区的铁丝网,如今正毫无准备地踏入丧尸的领地。
远处是肉眼无法估量的活死人军团,只要不小心发出一点动静,那些东西就会蜂拥而至,把他们撕成碎片。
洛钦转身看着身后那座坐落在省道上、已经半废弃的白塔,那扇门上爬满了红棕色的铁锈,一道锁顽强地守在门前。
水荔扬伸手一拽,那锁就立刻碎成了两段,似乎已经脆成了一片纸。
杂鱼
关于杂鱼:西元3000年,人类已经进入银河系时代。但由于科技的局限,和人生的有限,因此人类依旧被困于时间和空间的牢狱中,于古地球时代并无本质区别。随着资源的枯竭,历经千年的黄金时代终于临近尾声。强大而激进的日耳曼军团再次向世界露出了他们的獠牙,亚细亚和新罗马被迫应战。3022年,战争爆发。3032年,盟军装甲兵上校霍成功阵亡。3016年,16岁的霍成功带着他后世的记忆,再一次跨入了时间的长河中。于是,一切终...
雪未尽,已半生
那天的上京下了一场好大的雪,古卿意终是在大雪纷飞中走了出去……言斐自城楼注视着离开的那人,她没有回头,雪淋的她一身,也淋了他一身,共此雪,仿若共白头。......
求生悖论[无限]
三岁,纪惊蛰搬到蔚迟隔壁。 五岁,纪惊蛰生了一场大病,蔚迟一直觉得他后来脑子有点问题都是这场病害的。 八岁,纪惊蛰被人喊矮婆娘,蔚迟第一次打人。 十一岁,纪惊蛰的作文得了全市一等奖,题目是《住我隔壁的哑巴哥哥》,蔚迟第二次打人。 十三岁,纪惊蛰偷了他爸的钱包,带蔚迟去爬山,差点被山洪淹了。 十五岁,纪惊蛰的父母在车祸中去世,从此在蔚家蹭饭。 十六岁,纪惊蛰的身高超过了蔚迟。 十七岁,纪惊蛰一模英语31,蔚迟保送科大少年班。 十八岁,纪惊蛰消失了。 蔚迟开始发了疯似的找,用尽了一个十八岁男孩可以用尽的一切手段、废寝忘食地找,找了好多年。 找不到了。 在蔚迟终于要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,纪惊蛰拖着一个大红的行李箱,衣冠楚楚、花枝招展地回到了他面前。 这已经是五年后。 但蔚迟已经不想理他了。 可没过几天,地狱降临。 蔚迟站在他妈的办公桌前,正在应付纪惊蛰的消息轰炸,他妈忽然抬起头,眼角飞进太阳穴、嘴角咧到耳根,问他:几点了? [纪惊蛰]:? [纪惊蛰]:人呢? [纪惊蛰]:又不理人家。 [纪惊蛰]:嘤嘤嘤 竹马变天降 疯子(受)X少女(攻)...
上门女婿都市至尊
以下是为生成的相关内容:简介入赘三年,林羽在沈家饱受冷眼与欺辱,被视作毫无用处的废物。妻子沈梦璃对他态度冷淡,沈家上下动辄辱骂刁难。然而,无人知晓林羽实则是隐世古族的传人,身负绝世医术与高深武技。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,让林羽不得不展露实力。他凭借神奇医术妙手回春,救治重症患者;以强悍武技震慑宵小,化解重重危机。在都市......
长夜无尽夏
世人眼中,扶夏冷僻孤傲,如高山上纯净的苍雪,叫人不敢轻易肖想。 褪去铅华,他却自甘折翅,成为季晏承养在西郊别苑的一只笼中雀鸟。 8年蹉跎,扶夏在花圃种了满园的无尽夏。 曾灼灼祈盼花期的到来,向季晏承讨上一只戒指。 男人彼时不答,收起笑意在月色下抚上他的肩膀,只道:“最近是不是累了?出去玩上几天吧,还刷我给你的那张卡。” 直到季氏联姻的消息在城中不胫而走,扶夏手中画笔一滞,这才恍然明白——人哪里是不愿送戒指? 只是不愿将戒指,送给自己罢了。 夏至暴雨,花园尽毁。 如季晏承所愿,扶夏后来真的走了。 不是度假,而是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,没有带走任何行李,无声无息关上了别苑的大门。 异地他乡,两人再度重逢。 扶夏望向故人的眼眸已然冰冷,季晏承却毫不掩饰面上的惊喜,于人潮中紧紧抓住他的手。 扶夏问他何事,来人唇齿微颤,良久后竟是开口唤了他的小名。 一年花期又到,只听男人在自己耳边低声恳求:“宝宝,后院的无尽夏开花了,可不可以,跟我回家?”...
白头吟
冷风四起,正是初春,乍暖还寒的季节。一辆白色私家车从远处缓缓驶入内部道路,七八个空闲车位,车子没有选择往前停靠,却悄悄停在了最不起眼的隐蔽角落。稍许,车门打开,一只黑色高跟鞋从车内探出...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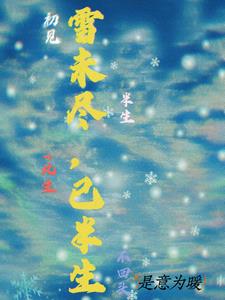
![求生悖论[无限]](/qs_html/img/48/48711/48711s.jpg)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