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
过天门 第55节(第1页)
洛胥呼吸偏重,他撑着身,没有抬起头。那双总是看起来游刃有余的眼睛藏在黑暗里,不露任何锋芒。
“好聪明,”他声音还是微哑,“你说得不错,我与他们的确有仇。”
这个“仇”字落在齿间,有几分森然的杀意。他没有反驳明濯,而是继续用了“他们”这个称呼,说明事实与明濯猜测得相差无几,杀他父亲的并不是一个人,而是一群人。
洛胥今年二十有二,十五年前他七岁,契约刚刚生效的时候,他父亲已经是强弩之末。他们知道受骗了又能怎样?那时别说让他父亲来霈都,就是让他父亲坐起身,都很困难。
“这世上有一种奇怪的咒诀,它既没有名字,也没有痕迹。”洛胥似乎在陈述天气,他眼皮抬起来,露出眼底深深的恨意。可是那恨意太冷、太深,更像是另一种没有温度的疯狂:“它施在人身上的时候,可以让对方感受到剜心挖骨般的疼痛。我父亲中了九道,每次发作,他都会独自待在静室里。第一年,他还有清醒的时候,第二年,他就疯了。”
黑夜寂静,两个人如似交颈,可是他们其实谁也碰不到谁。魂魄相许以后,两个人的心跳能重叠,可是其他呢?这样就算紧密相连了吗?
创造这个契约的二代君王明晞自己都没有搞懂,她最残忍的是错把占有当作了爱。疼痛无法使心意轻易相通,更可况还只是一个人在感受疼痛。
洛胥抬起一只手,没有碰到明濯,他隔空描过明濯的眉眼,像在重复那些煎熬的时刻:“我最后为他更衣的时候,他什么话都没有留给我,那一天我把他送入天海,他像雾一样消散了。”
那些日子里,洛胥的胸口每天都痛,有时候,他也分不清楚,究竟是他在痛,还是另一个人在痛。这该死的、可恨的狗链套着他,让他在每一个危机四伏的夜里都忍不住妄想,或许另一头的人也在感知他的痛苦呢?
“如果昨天你没有杀了他们,”洛胥说,“他们也走不出霈都。”
明濯的推断有一部分是靠洛胥的反应,他摸过洛胥的脖颈,也碰过洛胥的脸颊,可那并不是因为他对洛胥有什么爱意或痛意,他只是对洛胥有一点好奇。
比如现在,他抬指勾住了洛胥没有落下的手,衣袖下滑,露出的腕骨上还有白天的握痕。
“你看着我杀人,”明濯说,“你真奇怪。”
他琥珀瞳专注,看着那只手,好像勾这一下,也没什么大不了。
这次没有人攥衣领,但是洛胥的喉间还是在发紧。那勾住他的手指冰凉,像是越过那些不为人知的夜,在黑暗中,回应了他一次。
第70章 豹与豹赏你。
可惜回应只有这一下,明濯勾完手指就说:“讲完了就让开。”
洛胥半晌没动,他盯着明濯:“不让会怎样?”
“不怎样,”明濯微微屈膝,顶住了洛胥,“但是麻烦你,不要随便压在别人身上。”
洛胥说:“刚刚不是还要训我吗?”
杂鱼
关于杂鱼:西元3000年,人类已经进入银河系时代。但由于科技的局限,和人生的有限,因此人类依旧被困于时间和空间的牢狱中,于古地球时代并无本质区别。随着资源的枯竭,历经千年的黄金时代终于临近尾声。强大而激进的日耳曼军团再次向世界露出了他们的獠牙,亚细亚和新罗马被迫应战。3022年,战争爆发。3032年,盟军装甲兵上校霍成功阵亡。3016年,16岁的霍成功带着他后世的记忆,再一次跨入了时间的长河中。于是,一切终...
雪未尽,已半生
那天的上京下了一场好大的雪,古卿意终是在大雪纷飞中走了出去……言斐自城楼注视着离开的那人,她没有回头,雪淋的她一身,也淋了他一身,共此雪,仿若共白头。......
求生悖论[无限]
三岁,纪惊蛰搬到蔚迟隔壁。 五岁,纪惊蛰生了一场大病,蔚迟一直觉得他后来脑子有点问题都是这场病害的。 八岁,纪惊蛰被人喊矮婆娘,蔚迟第一次打人。 十一岁,纪惊蛰的作文得了全市一等奖,题目是《住我隔壁的哑巴哥哥》,蔚迟第二次打人。 十三岁,纪惊蛰偷了他爸的钱包,带蔚迟去爬山,差点被山洪淹了。 十五岁,纪惊蛰的父母在车祸中去世,从此在蔚家蹭饭。 十六岁,纪惊蛰的身高超过了蔚迟。 十七岁,纪惊蛰一模英语31,蔚迟保送科大少年班。 十八岁,纪惊蛰消失了。 蔚迟开始发了疯似的找,用尽了一个十八岁男孩可以用尽的一切手段、废寝忘食地找,找了好多年。 找不到了。 在蔚迟终于要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,纪惊蛰拖着一个大红的行李箱,衣冠楚楚、花枝招展地回到了他面前。 这已经是五年后。 但蔚迟已经不想理他了。 可没过几天,地狱降临。 蔚迟站在他妈的办公桌前,正在应付纪惊蛰的消息轰炸,他妈忽然抬起头,眼角飞进太阳穴、嘴角咧到耳根,问他:几点了? [纪惊蛰]:? [纪惊蛰]:人呢? [纪惊蛰]:又不理人家。 [纪惊蛰]:嘤嘤嘤 竹马变天降 疯子(受)X少女(攻)...
上门女婿都市至尊
以下是为生成的相关内容:简介入赘三年,林羽在沈家饱受冷眼与欺辱,被视作毫无用处的废物。妻子沈梦璃对他态度冷淡,沈家上下动辄辱骂刁难。然而,无人知晓林羽实则是隐世古族的传人,身负绝世医术与高深武技。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,让林羽不得不展露实力。他凭借神奇医术妙手回春,救治重症患者;以强悍武技震慑宵小,化解重重危机。在都市......
长夜无尽夏
世人眼中,扶夏冷僻孤傲,如高山上纯净的苍雪,叫人不敢轻易肖想。 褪去铅华,他却自甘折翅,成为季晏承养在西郊别苑的一只笼中雀鸟。 8年蹉跎,扶夏在花圃种了满园的无尽夏。 曾灼灼祈盼花期的到来,向季晏承讨上一只戒指。 男人彼时不答,收起笑意在月色下抚上他的肩膀,只道:“最近是不是累了?出去玩上几天吧,还刷我给你的那张卡。” 直到季氏联姻的消息在城中不胫而走,扶夏手中画笔一滞,这才恍然明白——人哪里是不愿送戒指? 只是不愿将戒指,送给自己罢了。 夏至暴雨,花园尽毁。 如季晏承所愿,扶夏后来真的走了。 不是度假,而是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,没有带走任何行李,无声无息关上了别苑的大门。 异地他乡,两人再度重逢。 扶夏望向故人的眼眸已然冰冷,季晏承却毫不掩饰面上的惊喜,于人潮中紧紧抓住他的手。 扶夏问他何事,来人唇齿微颤,良久后竟是开口唤了他的小名。 一年花期又到,只听男人在自己耳边低声恳求:“宝宝,后院的无尽夏开花了,可不可以,跟我回家?”...
白头吟
冷风四起,正是初春,乍暖还寒的季节。一辆白色私家车从远处缓缓驶入内部道路,七八个空闲车位,车子没有选择往前停靠,却悄悄停在了最不起眼的隐蔽角落。稍许,车门打开,一只黑色高跟鞋从车内探出...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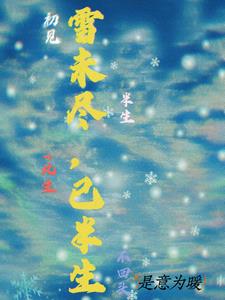
![求生悖论[无限]](/qs_html/img/48/48711/48711s.jpg)


